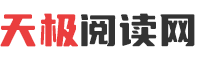“几位同志,我能和我儿子、姑娘单独聊聊吗?”
何大清安抚了雨水激动的情绪,看着赵同志、贺同志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,脑袋低垂,眼珠转个不停,目光就是不敢和军管会的人对视。
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很正常,在赵同志、贺同志眼里早已无所遁形。
果然,何大清抛家弃子来到保城,另有隐情。
赵同志一口回绝:“这恐怕不行,你们家的事儿有可能牵扯到他人犯罪,我需要向你求证一些细节。”
何大清一听要审问自己,以为自己的事情暴露了,**来抓自己了,两条腿已经不受控制打颤,面瘫冷酷的脸上渗出滴滴汗珠。
强打起精神,颤巍巍地跟在赵同志身后。
当见到儿子竟然不过来搀扶自己,反而转身追上赵同志,没看见你老子吓得都腿软了。
看着何雨柱,何大清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自己为了躲**,不连累儿女,都躲到人生地不熟的保城了,没想到自己的大孝子带着**的人,来抓自己。
何大清越想越气,对着何雨柱**就是一脚:“你个傻柱子,叫你傻柱子,你还真是个傻子。”
被莫名其妙地踹了一脚,两天来积攒的委屈和愤怒,何雨柱哪里还能控制得住。
但又束缚于父亲长年的积威和中国传统的孝道,何雨柱只能双眼血红狠狠地盯着何大清,两个拳头握了又松,松了又握。
何雨柱在心中暗暗发誓,这辈子绝对要比何大清过得好,绝对不让何大清像梦中一样,没尽到父亲的责任,还能常常摆父亲的谱嘲讽教训自己。
看见何雨柱仇恨的眼神,何大清火气更大扬起巴掌就扇了过去:“怎么着,翅膀硬了,想揍老子。”
赵同志挡在何雨柱身前,一把抓住何大清的手腕。
这算是见识到了,何雨柱口中混不吝的爹是什么样了。
何大清被儿子忤逆气得忘记了对**的害怕,斜眼看着赵同志:“自古老子打儿子就是天经地义,怎么着你们公安连老子打儿子也管。”
赵同志甩掉何大清的手腕:“真让你说着了,现在是新社会了,老子打儿子还真归我们管,知道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什么吗?”
“告诉你,就是《婚姻法》,里面就涉及对妇女儿童的保护,你要再无辜殴打……”
“赵叔,你让他打,以后再打也打不着了。”
没等赵同志把话说完,身后传来何雨柱没有一丝感情的声音。
做出了抛家弃子这等不耻事情,不仅没有一丝愧疚,还摆当爹的谱。
何大清这一闹,把何雨柱对他的最后一丝念想给也闹没了。
每一个字都犹如钢针一样,把何大清扎成了泄气的皮球,如同行尸一样跟着赵同志。
他只能在心中不断自我催眠:我没错,我都是为了他们好,长大了,他们会理解的。
进了东厢房。
“坐,不要紧张,我们就是向你核实点情况。”
赵同志坐在堂屋八仙桌的主位,指着对面的位置,示意何大清坐。
看着犹如审问逼供的场景,何大清忘记的恐惧又回来了,磨磨蹭蹭地坐下,**只敢坐在凳子边上。
“**,我们何家三代厨师,都是本本分分做人,老老实实做菜,真的没干过卖国求荣生儿子没**的事儿。”
“停!停!停!什么乱七八糟的,我问你,你答什么。”
赵同志掏出本子和钢笔,装作无事地打断了叫屈的何大清。
心中已经确定,何大清来保城,就和他恐惧下说出的这些话有关。
“你离家的时候都带走了什么东西?”
“我就带走了四季换洗的衣服,和三百万的现金。”
“详细说说都带了哪些衣服。”
何大清将自己带走衣服的数量、样式仔细地讲了一遍。
赵同志记录完,继续问道:“你离家的时候,给柱子兄妹留了什么?”
“我给他们兄妹每人做了一套被褥,一套秋装、一套冬装,还给他们留了十斤的腊肉、十斤白面、五十斤棒子面,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百五十万的现金,存放在邻居易中海那里。”
赵同志低头快速地记录着,和雨水讲得大体一致,不由得瞟了一眼窝在何雨柱怀里睡得很香的雨水。
经历了大喜大悲,小孩子早已身心俱疲。
何大清还没有反应过来,继续说着:“我已经跟我们食堂的后勤主任打好招呼了,让柱子接替我的工作,还叮嘱易中海,柱子入职的时候让他带着去,我估摸留下的东西和钱坚持到柱子出师,上班发工资还是绰绰有余的。”
一直旁听的何雨柱,现在心情非常复杂,既恨何大清抛家弃子,又因他的这些安排有些安慰,至少没有真的不管自己兄妹。
“认字吗?”
“认字,厨子不认字,还怎么看菜谱。”
赵同志把本子和笔递给何大清:“把你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,新添置的东西要标注在哪里购买的。”
机械地接过本子和笔,何大清再笨,现在也知道家里出事了。
“赵同志,我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?”
“在你走以后,到柱子回家的这段空档时间,你们家遭到了入室偷盗,我们现在初步怀疑是同院子的邻居所为。”
赵同志看了一眼处于暴怒边缘的何大清:“你现在是车站公安局辖区的住户,我们需要你的报案材料,才能前往京城,要求当地的公安局协助调查。”
何大清面瘫的脸上带着杀意,激动地站了起来:“赵同志,我报案,只要让这些畜生遭到报应,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行。”
赵同志将何大清按回凳子上:“现在是新中国,不兴旧社会那一套,我们人民公安也不是旧社会的巡警,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,依法抓捕犯罪分子是我们的职责。”
回到座位后,赵同志盖上笔帽,语气平和问道:“能聊聊你跟着白寡妇来到保城的原因吗,我想一个白寡妇还不至于让你抛家舍业。”
见何大清紧张地低头不语,赵同志劝道:“何大清,你不要有什么顾虑,一年多,你们街道都没有抓捕你,就说明你没有问题。”
“其实不说也没关系,你身为新来住户,这边的街道也会把你的来历查清楚的。我是替柱子问,他总归还是要回四合院生活的……”
没等赵同志把话说完,何大清已经明白话中的意思。
“赵同志,谢谢您!”
何大清起身就给赵同志鞠躬,这一礼,拜得是心甘情愿。
“我何大清出生的时候大清还没亡,也经历过北洋、张大帅、小鬼子、刮民党,就没见过这么仁义的**。”
何雨柱见何大清给赵同志鞠躬,抱着雨水也起身鞠躬,他也想知道到底是谁在算计何家。
赵同志急忙扶住何大清、何雨柱。
“快起来,咱们不兴这个,人民的**,就是保护老百姓的。”
何大清坐下长长呼出一口气,缓缓讲述起来。
“半年前,上班的时候,几辆拉着汉奸游街的卡车从我身边经过,在卡车上我看见以前的掌柜。”
“我呢,在京城勤行也算小有名气,曾经也给鬼子、汉奸、刮民党做过饭,我就怕有一天自己也被抓起来。”
赵同志无奈地笑了笑:“你这就是自己吓自己,沦陷区的多少老百姓被鬼子逼迫做过事,难道都要抓起来。
“被人民**抓起来的,都是投靠鬼子有实证的。”
何大清自嘲地笑了笑了:“赵同志,您说得太对了!”
“那一天我被吓得跟没了魂儿似的,晚上找易中海喝酒,他建议我不如先到外地躲躲……”
话说到一半,何大清变得非常激动:“赵同志,是易中海!绝对是易中海!”
“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,他刚刚让我出去躲躲,没半个月就有人把白寡妇介绍给我。”
何大清自嘲地道:“我何大清自诩聪明,没想到却被易中海这个伪君子啄了眼。”
何雨柱也被这结果惊呆了,他怀疑蛮不讲理的贾张氏,怀疑过二流子的麻三,甚至怀疑过贪小便宜的阎埠贵,就没怀疑老好人易中海。
在梦中,自己也多受易中海照顾,是何雨柱在四合院少有的温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