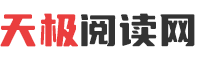第1章
新来的班主任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眼中满是不屑。
「听说你爸爸是个皮条客,妈妈是个**。」
「作为他们孩子的你......该是如何肮脏不堪?」
我没有反驳,准备接受这一轮新的羞辱。
只是我心中暗暗发誓,我一定要让他们后悔。
1
我家很穷,家里只有一亩三分地,荒废了许久。
家中五个孩子,两个姐姐已经出嫁,还有一个妹妹早些年的时候送了人,家中只剩我一个女孩。
唯一的哥哥,整日游手好闲,叼着根狗尾巴草从村头到村尾,调戏落单的少女。
一家四口靠着我妈制衣厂里每月两千块的工资过活。
我爸嗜酒如命,好赌成性,可逢赌必输。
每次输了就气急败坏,喝着两块钱一斤的酒,喝醉了回家就会打老婆孩子。
十二岁那年,我爸输了很多钱。
回到家对着妈妈就是一顿拳打脚踢,家里的碗在我爸的大手下碎了一地。
我妈满脸鲜血,哭着求他不要再摔东西了,那些都是钱。
实际上,家里除了那几只碗也没什么能摔的了。
我死死抱住我爸的腿,浓烈的酒味熏得我想吐。
「不要再打我妈了!」
可他不予理会,一脚将我踹翻在地。
地上散落的碎片沾满鲜红的血,我不敢喊疼,怕迎来一顿新的毒打。
男人的怒吼声,女人的哀嚎声,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彻夜响起。
这场暴行在我爸的疲惫中渐渐停止,寂静的夜晚,呼噜声和窗外的蛙鸣声一唱一和似的,实在可笑。
我妈将我抱在怀里,将随手摘来的草放在嘴角嚼烂,搓成墨绿色的草团敷在伤口上。
**辣的,伤口仿佛像火烧般。
村里到处是这种不起眼的小草,每次受伤,村里的人就会用它止血。
可是这不见得有用,捂上了,我反而觉得更疼了。
「这么多年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,忍忍就好了。」
她低喃着,像在说给我听,又像说给她自己听。
忍忍,真的会变好吗?
我望着她,她的脸上到处是淤青,手臂肿得好似注满了水一样,鼓鼓的。
身上原本靓丽的衣服早就褪了色,硬邦邦地皱在一起,一点温度都没有。
那瞬间,温热的液体从眼角滑落,一滴一滴滑落在我手臂上。
「妈,我们离开这里吧。」
我想逃离,逃离这个满是痛苦的牢笼。
「你爸他以前不是这样的,他以前很好的......」
我妈又开始回忆,年轻时她和我爸异常恩爱,又开始期待未来。
可是,我爸不是第一次这样打她了。
第二天,我妈像往常一样起早准备早餐,我爸一脸愧疚地向她道歉。
「翠玲,昨天是我不对,喝酒犯了浑,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」
道歉,发誓,送野花。
像以前一样,打一巴掌送一颗枣。
我妈却极为受用,甜甜地笑着对我说:「你看,我就说你爸很好的。」
2
可是当晚,我爸悄悄拿着家里的地契,以五千块的价格,卖给了当地的恶霸。
我爸拿着钱跑了。
看着眼前来收房子的人,我妈颤抖着双手,接过那张薄薄的纸,上面有她的手指印。
我妈不识字,稀里糊涂地被我爸卖了房子都不知道。
这个房子不值钱,是早些年外公外婆留给我妈的房子。
这里地处偏僻,镇上的人来慰问困难户经常会把我家落下,因为找不到。
我妈百思不得其解,他们要这个破房子有什么用?
可是恶霸从来不讲道理,我们的东西来不及收拾,被他们扔进河里。
无家可归的我们来到奶奶家,房子是一样的破,却更小了。
奶奶一口一个乖孙地摸着我哥的头,饭桌上挑挑拣拣好半天才翻到一条肉丝,全部放进了他碗里。
奶奶看着我,满目慈祥:
「女孩子啊要少吃肉,瘦点,才好嫁。」
我习惯地低下头,我妈却满脸愧疚。
为我做了这桃花糕,味道是极好的。
门前的春桃落了一回又一回,吃在嘴里苦涩极了。
城里的人带回我爸的消息,我都快忘了还有一个爸。
没有他的生活,除了奶奶的挖苦,实际上我们过得还不错。
他们说我爸在城里做起了皮条客,赚的钱多得足够花一辈子了。
我不懂皮条客是什么,但他们在嘲讽,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
奶奶听到我爸赚了钱,在村里扬眉吐气了起来,听到谁都要拉着吹嘘上半天。
可是我爸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,家里的米缸都要见底了。
这个家仍然靠着我妈,但奶奶依旧不喜欢她,也不喜欢我。
同为女性,却看不起女性。
从我记事起,奶奶就没给过我妈好脸色。
在我们村,生不出儿子的女人是会让人笑话的。
即使我妈最后生了儿子,我奶奶却因为这事一直给她难堪,女孩太多了,丢人。
我爸走了,奶奶责怪我妈没有本事,留不住男人。
她一大把年纪还要被村里的其他老人笑话,一切都拜我妈所赐。
我妈在一旁低着头剥着玉米,默不作声。
今年雨水多,发了大水,淹了玉米地。
连同这片玉米地倒下的,还有我哥。
3
他反复高烧不退,除了吃饭时间就是在咳嗽。
镇上的医生说见了白肺,救治需要好几万,让准备好钱。
我妈到处求人,四处借钱。
可是穷人认识的都是穷人,哪里有钱能借到呢?
一筹莫展之际,奶奶把棺材本翻了出来,黑色塑料袋包着。
里三层,外三层,摊开一看,所有的钱都被老鼠咬得零零碎碎。
五千块,全没了,奶奶坐在地上痛哭流涕。
她埋怨老鼠,埋怨我妈没看好儿子,埋怨我妈没本事。
姐姐们听闻这事,顾不上婆家的怨言,东拼西凑地偷偷将钱塞给我妈。
妈妈感激涕零地收下了,虽然不够,但是足以抵大部分费用。
可是,这钱在我妈手上还没捂热,当晚家里就遭了贼。
睡梦中听到我妈撕心裂肺地哭喊:
「这是我孩子的救命钱,求求你,求求你......」
我妈整个人瘫软在地上,眼神空洞,失去了生气。
那个贼跑得很快,虎背熊腰的,身影看起来熟悉极了,在转角处完全没了踪迹。
我让我妈报警,但这事却不了了之。
村里没有摄像头,丢了就是丢了,还没有谁家丢东西了能找回来的先例,更别说是钱了。
屋漏偏逢连夜雨,我被哥哥传染了。
止不住地咳嗽让我彻夜难安,我妈望着我,哭诉着她多不容易:
「家里没钱,你怎么这么不懂事,在这个时候生病。」
「让我该怎么办啊......怎么办......」
走投无路,我妈想到了我爸,她托人往城里传话,给了那人好几只鸡。
可是那人回来了,支支吾吾地。
得,没戏。
「兴许你爸过得也难......」
我爸那种人,过得不好早就灰溜溜地回来了,怎么会在外面受苦呢?
我爸不管我们,只有我妈一个人发愁,整日里唉声叹气。
直到某天一大早,我妈穿上长裙,难得打扮了一番,容光焕发。
4
我妈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美人,我很早就知道。
我爸走后的这几年,我们家孤儿寡母的,遭人惦记。
村里不少老光棍觊觎我妈的美貌,半夜里总有人爬我家围墙。
有天闯进来一个老头,扯着我妈的衣服。
我疯了一般地,跑进厨房里拿着菜刀,将那人的手臂砍了好几刀,鲜血淋漓。
我妈笑着说,那时的我,真的很像一个杀红了眼的杀人犯,她都怕我几分。
自那以后再没有人敢半夜翻进我家围墙,我们也过上一段安生日子。
记忆里,我妈很少打扮,更别说如今那么艰难的时刻了。
她走到床边,一脸坚定地对哥哥说:
「我的狗崽儿,不要怕,妈妈一定会救你的。」
我看着她的身影,消失在夜色中。
我在床上翻来覆去,难以入梦。
钟摆上的时针停在了三上,滴滴的声响在寂静的夜晚中异常清晰。
门外传来喇叭的声响,汽车扬长而去。
门被轻轻推开,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扑面而来,呛得我猛烈咳嗽。
月光洒在我妈脸上,疲惫不堪。
四目相对,那张脸笑得很是温柔:「暖暖,我们有钱治病了。」
我不敢问钱是哪里来的,可是我不问不代表别人不会问。
第二天一大早村里传遍了这件事。
村里的女人站成一排,怀中抱着留着口水的小孩,对着我妈指指点点。
男人们盯着我妈,有些嘴里还吹着口哨。
他们说我妈不检点,昨晚去镇上陪男人了。我妈手足无措,不敢看他们,只是低声说着」我没有」。
我羞愧极了,挣脱我妈的手,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家。
这病,不治也罢,死了也好。
累得气喘吁吁,家门口的轮廓近在眼前,我回头期待地看了一眼。
我妈没有追来。
我躲在厚棉被里歇斯底里地哭泣,被褥湿了一大片,为什么要让我遭遇这些事。
听奶奶说,哥哥住院后病已经好了一大半,过两天就要出院了。
而我虚弱得无法自己进食,奶奶没有管我,整日不知在院子里敲着什么东西。
直到这天,家里来了一对老夫妻,奶奶一脸殷勤地为他们倒水。
五
这两人我是认识的,隔壁村最有钱的养殖户,靠养猪赚了不少钱。
前些日子死了儿子,听说是醉酒车开进了泥塘,淹死了。
他们看着我,一脸满意地点点头,将一个整齐的纸袋子放在桌上,红色的纸币漏了出来。
「暖暖奶奶,这里是六千,你数数。」
「哎呀,你们说的是什么话,你们给的肯定够数。」
奶奶笑得合不拢嘴,大拇指往嘴里沾了沾口水,拿着那打钱一张一张数了起来。
那对老夫妻站我身前,一脸慈祥:「暖暖,跟了我儿,以后保准你吃香喝辣的。」
他们,在说什么?
他们儿子不是死了吗?
我疑惑不解地看向奶奶,她拉过我的手:
「暖暖丫头,你是个懂事的,家里穷,没钱给你治病了,你要是盼着我们好,就开开心心地去给他们家配个冥婚,你妈日子还能过得舒坦点。」
听着奶奶的话我不寒而栗,她要我嫁给一个死人?
她盼望着我死后,给那家人的儿子配个冥婚?
不,我不要。
容不得我拒绝,那对老夫妻给奶奶多付了一千块,让我尽早去陪他儿子。
他们将我抬起来,装进蛇皮袋里,化学肥料的味道**着我的胃,吐了满身,意识渐渐模糊。
这辈子,就这样了吧?
「暖暖!暖暖!」
急切,慌乱不安。
那是我妈的声音,她也是在意我的吧。
她和奶奶起了争执,质问奶奶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
各种东西碰撞的声音,女人的呼喊声,混在一起。
我渐渐晕了过去。
睁开眼,见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,蓝色的围帘,消毒水充满鼻腔。
医生责怪着我妈,再晚来一步,我就没了。
我妈明显打扮过了,但依然遮不住她眼中的疲惫。
她唯唯诺诺地点着头,对医生鞠躬道歉。
我想问问医药费是不是我想的那样,她又去镇上陪男人了?
可是我不敢......
她救了我的命,我有什么好矫情的。
后来这事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,就像没发生过一般。
可是,这些事早已传遍了村里,甚至学校。
6
我今年初三,却没有一个朋友。
同学们对我指指点点,辱骂我妈,嘲笑我。
「你的妈妈是鸡,你也是鸡。」
我不知道怎么反驳,她们说的好像是事实。久而久之,我习惯了校园霸凌,习惯了不反抗。
脱衣服拍视频,抓头发,逼我吃厕所里的东西….
这一切我没有跟我妈说。
她也许还不知道,她是我痛苦的源头。
她每次彻夜不归,我们便会过上几天好日子,可这也意味着我妈承受了更多。
当她再次凌晨三点回来时,我再也忍不住,上前推开那个老头。
在我看来,他们仿佛在亲吻。
那一刻我觉得恶心极了,我不再让我妈碰我,也不愿意再见到她。
我讨厌呆在家里,也讨厌学校。
我经常逃课,在学校外面的小卖铺一呆就是一整天。
这天,一个戴着眼镜,气质儒雅地男生找到我,他说他是新来的班主任。
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眼中满是不屑。
「听说你爸爸是个皮条客,妈妈是个卖的。」
「作为他们孩子的你......该是如何肮脏不堪?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