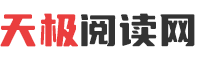咚——!
一声巨响,泳池里水花迸溅。
落水声夹杂着岸上的摇滚音乐和尖叫的人声,一片混乱。
“有人落水了!”
“是谁?落水的是谁?!”
“靠,怎么是他啊!快快快,把人捞起来,他不会游泳!”
耳膜被水堵住,所有吵闹声退去,变成闷响的轻语。
冰冷的水流化身从地狱生长的荆棘,缠住收紧,挤掉少年肺部残留的氧气。
少年只在水里扑腾不到半分钟,便犹如失去动力的机器,静止沉默,任由身体一点点往池底沉落。
-
头疼,喉咙痛,连带着眼皮还有点辣。
安意从一片混沌中醒来,闭着眼从床上坐起。
他不知道昨天加个班,怎么就突然晕过去了。
打工人,打工魂。
倒在地上失去意识之前,他还在担心工程二期的设计图是不是忘了保存。
不行,得赶紧回工位上看看。
安意睁开眼,顿住两秒后,又重新闭上眼。
我眼睛已经花成这样了?
做好一番思想工作,安意试探性地睁开左眼,确认眼前事物依旧如故,唰地睁开双眼,愣愣地盯着自己身处的房间。
此刻的安意置身在一间华丽复古、欧洲中世纪风格的房间里。
蕾丝花织的床,复古厚重的地毯,以及墙上那幅看起就不是社畜能买得起的油画……无一不在提醒着他:有钱,有品位,和他不搭。
不是吧。
现在医院装修都这么豪华了吗?
不对啊,他现在最该担心的不该是住在这种配置的病房里一晚得多少钱吗?
靠。
他骂骂咧咧下床,一边穿鞋一边在心里谴责同事太不人道。
一阵门响。
安意朝门口方向一看。
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推门而进,看见他的一刻,眼圈立刻殷红,脚步急促地走过来,挥手把他轰上·床。
“醒了下床干什么?上去,上去。”
安意架不住男人连搡带推,只好又乖乖躺回床上。
男人长相周正,看着面慈心软,眼睛只有豆子大。
不过,这所医院的医生都**白大褂的吗?
这也太不专业了吧。
男人坐他床沿,抹眼擦泪地拽着他的手,哽咽道:“安安,你这次真把爸爸给吓坏了……”
不是。
等等。
什么玩意儿?
男人继续哭诉:“为了一个男人,你连爸爸都不要了吗?”
安意倏地抽回手。
这年头,住院还给送爹的吗?
男人茫然地抬眼看他。
安意皱眉:“不是,叔,你谁呀?”
这话犹如一把重锤砸在安宝成的太阳穴上。
没想到安意居然疯成这样?
他摇摇摆摆从床沿上起身,眼里的茫然质疑转瞬成惊惧怒火:“你说我是谁?你连你爹都不认了?!”
“你放屁!”安意反驳道,“我从小就没爹!”
啪。
一阵风刮来。
安意左脸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。
脸上立刻像扎入无数银针一般,刺痛烫热。
他捂住左脸,猛然看向中年人,怒道:“你有病吧!我要投诉!”
-
医生收起听诊器,随后走出房间。
医生前脚离开,安意后脚就悄悄下床,耳朵贴在门后偷听外面走廊两人的谈话。
“心脏机能方面没什么问题。大脑是否正常,还是建议带令郎去医院做个脑部CT。”
“好,辛苦你了。”
安宝成声音带着一点疲惫。
安意轻手轻脚地躺回床上,盯着彩绘天花板,一脸的不可置信。
靠。
他居然穿书了?!
《恶霸校草独宠我》原是隔壁女同事的一本闲暇读物。
安意纯粹会碰这本书,完全是因为他那天无聊,设计稿已经发给甲方审核,可甲方当天有事,他便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可以摸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