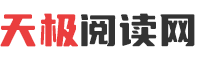马车一路驶向镇国公府。
车舆内铺着披绣百花地毯,又熏着香,不多时,陆轻竹便阖了双眼,躺在卧榻上睡着了。
等醒来时,就看见秋水安静的候在一旁。
陆轻竹揉了揉眼睛,一双美目带着浓浓的困意:“秋水,已经到了吗?”
“姑娘,已经到了。”
陆轻竹透过前方帏幔轻摆的间隙,看到了镇国公府门前的两座大石狮子,闻言,才渐渐清明起来。
“秋水,什么时辰了?”
“姑娘,午时了。”
陆轻竹微微睁大杏眸,她竟在马车中睡了一个时辰。
秋水见她这副模样,轻笑道:
“奴婢看姑娘睡的那么香,实在不想打扰。”
这一觉确实香,醒来时周身畅快,舒适不已。
秋水向来宠溺心疼她,估摸着是看自己太疲倦了,所以才不忍心叫醒自己。
陆轻竹想罢,掸了掸裙摆上的灰尘,又优雅细致地将斗篷穿上,就着秋水的手下了马车。
“秋水,一会儿我们走后门,免得被府里的人看到,若母亲知晓了,定会为我担心。”
谁知秋水眸色复杂,酝酿了好久才道:“姑娘,夫人早就知晓你上午哪里去了。马车停在镇国公府门前时,娟儿姑娘来问过奴婢,奴婢照实回答了,后来娟儿姑娘又来回话,说**如此困倦,让人先暂时不要打扰。”
这是母亲能做出来的事。
外人都道镇国公府的当家主母不苟言笑,雷厉风行,只有陆轻竹知晓这只是母亲的保护色而已。
这么多年来,父亲一直驻守漠北督统,一年至多回来一两次,诺大的镇国公府全靠母亲打理。
若她只是个和蔼可亲的女子,万万撑不起镇国公府的门庭。
而陈氏也仅仅只对外人不假辞色,对陆仪和陆轻竹温善到了极点。
这么多年,母亲只在昨日她的婚事上强势了一些,再无其他了。
如今母亲不仅要为府里操心,还要为她担忧,这让她生了一抹愧疚。
当即也顾不上如今的模样了,只想去正院给母亲问个安,好全母亲的慈母之心也全自己的子女之孝。
陆轻竹穿过帘廊,不多时便到了陈氏的正院中。
娟儿见她来了,含笑道:“姑娘,您醒了。”
“娟儿,我醒了,母亲可在屋里?”
“在的,在的。”
陆轻竹总觉得娟儿的眼神中略有深意,可她已无心考究。
陆轻竹拂过珠帘,杏眸儿在触到屋里的人时,蓦地一震,良久,红了眼眶。
“父亲……”
屋内的罗汉榻上坐着一位魁梧稳重的中年男人,双眼如电,炯炯有神。
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年初,而如今已是十一月了,再过一月,又是新的一年。
看到女儿激动的模样,镇国公亦是控制不住思念之情,但到底能稳住情绪,只唇角勾起一抹笑容,轻声道:“轻竹,为父和你娘可等了你很久。”
陆轻竹刚想问父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,可听了父亲的话,一时竟不好意思起来。
陈氏起了身,上前抓住陆轻竹的双手,柔声道:“轻竹回来了,今早去宁安寺所为何事?”
闻言,陆轻竹双眸闪烁了几下,支支吾吾随意编了一个理由搪塞了过去。
镇国公还坐在主位,听了陆轻竹不甚走心的借口后挑了眉峰,低沉的嗓音带着几许调侃:“听说轻竹已有了心上人,父亲十分好奇,究竟是哪家的臭小子竟得到了我女儿的芳心。”
“轰——”
陆轻竹的脑袋嗡嗡作响,一会儿看看母亲,一会儿看看父亲,只感觉少女的一腔心事在长辈面前展露无疑。
“父亲,母亲,你们在说什么呢?”
镇国公有意打趣女儿,见女儿听了他的话后怔懵在原地,又是脸红又是着急,手足无措的样子甚是可爱,不免心上有些疼惜,轻声道:“行行行,既然轻竹不愿说为父也不勉强。”
陈氏嗔了他一眼:“侯爷,你就别再说了。”
“好好好,是为父的错,轻竹,到了你们这个年纪,儿女情长本也正常,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如你哥哥那般不近女色,冷淡无情,为父觉得你这般样子才是个正常孩子。”
这旁敲侧击的暗讽不仅陈氏听懂了,陆轻竹也听懂了。
对于跟长辈一起讨论陆仪的私事,陆轻竹觉得不大自在,脸上现了几分窘迫。
倒是陈氏瞪了他一眼,好似在说有完没完,镇国公当即哂笑一声,不说话了。
见镇国公终于消停,陈氏挽了女儿的手坐于一旁的软榻上,眸中带了几丝怜爱:“轻竹,昨日我想了一晚上,嫁人确实是大事,但为的不是让你嫁人,而是让你幸福,刚刚我与你父亲商议了许久,见你对你那心上人一往情深,所以想让你父亲入宫请了旨意,成了你的心意如何?”
陈氏昨晚辗转反侧,忘不了自家女儿的泪眼。
若只是为陆轻竹求一门婚事,对于他们镇国公府而言太过简单。
两年前陆轻竹刚刚及髻,世家大族们闻风而动,纷纷想与陆轻竹定下婚事,陈氏一一考量了很久,都未有自己所满意的人选。
其中她最满意的宁国公府的世子孟怀仁似乎对自家女儿无意,宁国公府的夫人几次来镇国公府做客都未提及此事,她便也打消这个念头。
那日陆仪来她院中,说若是再不给陆轻竹定亲,她要变得魔怔了,当即吓的陈氏思索起此事。
但昨日,陆仪的口风又变松了些,似乎对于给陆轻竹急忙定亲一事没那么急迫了。
陈氏看出了一丝端倪,估摸着与女儿的心上人有关,今日镇国公一回来,便将此事说给了他。
若是能成全女儿的一腔爱意,做爹娘的付出些什么也无所谓。
陈氏见着陆轻竹听闻此言后,一时怔在原地。
陆轻竹心上不知是开心还是不开心,总归是极紧张的,嘴唇蠕动了几下,良久,才发出一道怯怯的声音:“这……还可以如此吗?”
镇国公笑笑:“自然,只要那人人品、才能过关,不论贫贱,为父都不会阻挠你。”
才能自是一等一的好,是说了名字就能让人折服敬佩的存在。
而且与哥哥是密友,人品自然也差不了哪里去。
陆轻竹恍惚间好似看到了自己与萧冕定亲的一幕。
她眸中生了几抹期盼:“谁都可以吗?”
兴许是她的眼神太过炽热,镇国公察觉到了一抹不对劲,思索了良久,道:“亦不是所有人都行。”
陆轻竹吐了口气,这结果也在自己的意料之中。
父亲手握重兵,一直为皇帝忌惮。
若是父亲为她入宫请旨,对象亦是手握重兵的萧冕,不知晓皇帝该如何猜想父亲。
最重要的是,萧冕并不是皇帝的旨意就能强迫的了的。
与其到时候因为此事大家都不安宁,还不如顺其自然的发展。
她知晓萧冕对她并无情意,她只想靠着自己的努力让他喜欢上自己。
想罢,陆轻竹颔首,“此事父亲无需担忧,轻竹自会努力的。”
陈氏与镇国公对望一眼,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诧异,慢慢的,眼眶中露出了几缕为人父母的欣慰。
陆轻竹在房中小坐了一会儿,想着为母亲和父亲腾出一些相处的时间,加上实在忍受不了裙摆处的泥泞,跟二人福了福身,带着秋水离开了正院。
-
陈氏静静凝视着陆轻竹的背影,因女儿的回答而生了一抹感叹,越发觉得陆轻竹已有了陆仪的风范。
在陆轻竹之前,陈氏还有过一个女儿,只是没养到三岁便没了。
后来实在伤心不已,去往普陀寺祈愿,老天眷顾,三个月后,她诊断出了两个月的身孕,十月怀胎,诞下了女儿,取名轻竹。
家中只她一个女孩,自是娇生惯养,谁知不小心将这孩子养成了任性妄为的性子。
一次,陆轻竹看中了户部侍郎女儿周燕手中的风筝,那是那女孩兄长亲手给她做的,周燕说什么也不给,陆轻竹一边哭一边抢,被陆仪逮住了。
陆仪那年十二岁,小小的脸肃然生畏,骇人的将陆轻竹吓的差点晕过去。
陆仪定定看了陆轻竹很久,冷冷道:“陆轻竹,谁教你这么霸道的?”
“哥哥,我……我……”
陆仪那时刚刚被陈氏批评对陆轻竹太过冷淡和严厉,所以不由的,将怒气带到了陆轻竹身上。
陆仪眉尖一拧,不知想到了什么,缓声道:“昨日哥哥教了你一句话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,轻竹可知晓是什么意思?”
陆轻竹怯怯的摇摇头。
陆仪突然叹息了一声,掌心在妹妹头顶上拍了一下,温和道:“现在不懂也无事,以后就会明白了,哥哥相信轻竹长大后会是个温婉懂事的女子。”
陆轻竹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
也是自那之后,陆仪认为自家妹妹的心性出现了问题,开始亲自教导,后来无论何时何地,都要把她带着。
记忆中那个顽皮的小姑娘也不知何时就长大了。
“时间过得真快啊,侯爷。”
镇国公揽着陈氏坐下:“夫人,子仪和轻竹都被你教的很好,你辛苦了。”
陈氏笑了笑,抚了抚他的手背:“夫君才是辛苦了,自武安侯去后,您撑了这么多年,如今,容王羽翼丰满,您对得住武安侯,对得住大彦了。”
陈氏肩头一沉,男人埋在她肩侧,良久才抬起头,眼眶红红的:“夫人,还是你最懂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