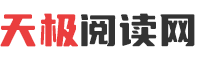庆国。
正月初一,正是全上京最喜庆热闹的时候。
不管是大户还是小家,都张灯结彩,喜庆非凡。
秦安头发凌乱浑身染血,麻木地从冰冷血腥的斗奴场内虚弱走出。
他身前不远处,典属官便冷着脸朝他喊道:
“秦安,赶紧滚过来,裴国公府来人接你了!”
他手里握着半截断匕,鲜红如血,上面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缺口和裂痕。
这是他生存下来的武器。
他抬起头,眼睛通红,眸光里闪过又惊又悲怆的神色。
稍纵即逝,眼底却死寂一片。
裴国公府,既是他日夜翘盼,又是心灰意冷的地方。
他曾是国公府最寄予厚望的嫡世子,裴安。
可这一切,自从三年前裴焕的出现。
爱他的人,皆面目狰狞地抛弃了他。
“裴安,你根本不是我们国公府的世子!你是卑贱奴婢生的野种!”
“焕儿才是我们国公府的嫡世子,可怜我儿在外苦了十七年。”
“阿安,不要怪阿姐狠心,终究是你欠阿焕的......”
这些话犹在耳边,让他认清现实。
十七年前,福安寺纪元方丈给国公夫人腹中胎儿卜挂告知。
即将出生的国公府嫡世子命格尊贵,乃是天之骄子。
但他身带煞气,若是留在家族中,迟早祸害整个家族。
所以需要把他送到别庄避难月余,吉时到由纪元方丈开坛做法去除煞气。
于是,裴安刚出生,就连国公夫人都未来及瞧一眼儿子稚嫩的模样。
便被抱去了别院,则由国公府内的乳娘秦兰照料。
而三年前,乳娘因良心不安,惭悔地跪在整个国公府人面前,揭露出她因私心将自己的孩子与真的嫡世子调换。
甚至不惜身死证明,裴焕才是真世子。
那一天,整个国公府上上下下所有人,皆眼露鄙视。
他们看他的表情,仿佛是在看一只肮脏低劣的野狗。
国公夫妇似念及他们十七来的亲子之情,当众宣布他依旧是国公府的世子。
同时他也是裴焕的阿兄。
就连一向疼爱他的阿姐,扬言他始终是她的胞弟。
而当他们亲眼见裴焕失手推倒了太子良娣,导致其腹中皇孙胎死腹中。
而裴焕身旁的家奴却当众咬死他是那个罪人时……
他们沉默了。
太子雷霆之怒,将他丢进这个野性撕杀奴命斗,贵族嗜血闹欢颜的斗奴场。
“秦安!耳聋了?”
典属官看见他没有回应,厉眉催促:“可别让郡主好等。”
秦安收敛思绪,将断匕往衣袖里藏了藏。
似一个傀儡跟在典属官身后,走出了他拼了命都要离开的斗奴场。
斗奴场外,一辆奢华马车旁正端站着一位貌美娇媚的女子。
容貌与国公夫人有五分相像,雍容高雅。
那是他的阿姐,裴钰。
当看见典属官带着浑身狼藉的秦安走近。
裴钰瞳孔颤动,眼角盈满泪水:
“阿……安?”
她在确认,眼前满身血渍,脏乱不堪,枯瘦似乞丐的人。
是那个三年前锦衣玉食、骑马游街,享尽荣华富贵和尊宠的国公世子,她的弟弟裴安吗?!
秦安神情寡淡,欠身行礼:“奴才秦安给郡主请安!”
三年前,不管他如何歇斯底里自证自己不是罪人。
她们却紧紧将裴焕护在身后,始终不曾替他辩证一句。
自此后,裴安就死了。
此时的秦安与他们云泥殊路。
见秦安如今一副奴才样卑微、低贱、肮脏......
裴钰刚迈出的脚步一滞。
她只觉得咽喉被无形的铁钳扼住,胸口窒闷得几乎喘不上气,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
她顾不上失态,急步扶起秦安。
丝毫不嫌弃他身上散发出浓烈刺鼻的腥臭味。
“阿安,快给阿姐看看?你哪里受伤了,怎流这么多血,疼不疼……”
秦安后退避开,垂着脑袋低声道:“郡主尊贵,莫脏了您的手,奴才无恙。”
他身上溅染的血,是同他卑贱奴隶的血。
而他的血,在被丢进斗奴场的那两年流干了。
此时的他,就是一个为了活下去的冰冷空壳。
裴钰的双手顿在虚空中,脸色微微沉凝下来。
是在怨恨她们当年推他出去顶罪吗?
沉吟片刻,敛起不悦,露出几分愧疚。
“阿姐......知道你受委屈了,但现在不是闹孩童性子的时候。”
“祖父无时无刻念着你,正是因为你,祖父近些时日身子越发不好,怕是很难挺过九春。”
见秦安不为所动,语气又软了几分:
“阿安,祖父这些年四处奔波寻求良药,成功让太子妃怀上皇孙,以此保你一命。”
“太子盛悦,这才特赦了你的死罪。”
她再次朝他伸出手:“来,随阿姐回家吧。”
她希望祖父为裴安的付出,能得到对方的回赠。
比如,不在埋怨三年前那件事……
秦安怎会不知她的意图。
说来说去,她们始终认为——
他欠裴焕的,欠整个裴国公府的。
秦安垂着的脑袋下,嘴角扯出一抹凄凉的笑意,将双手负于背后。
再次弯下腰恩谢:“多谢老国公的恩情,多谢太子的恩典。”
声音不带任何感情,似在谢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
裴钰再也忍住胸腔内的火气,瞪圆双眼:“阿安,你何必如此作践自己!”
虽恼火秦安的疏远,但更恼他不领她们的情:
“我们从未在意过你那低贱的身份,甚至还当你是裴府的世子。虽当年是阿焕闯了祸,但他已受了十七年的苦,我们裴家怎能让他丢了命。”
“你是阿焕的兄长,是裴家养育了你,给了你常人子弟无法拥有的生活。现如今,祖父愈发救你出了斗奴场,你怎能如此记恨我们?”
“你再看看,你现在这般伏低贱卖的姿态,枉为裴国公的世子,简直玷污了国公府的门楣!”
一句又一句谴责的话语犹如尖刀般凌迟着他的心脏,让他认清楚现实。
他不是裴国公府的裴安。
是家奴乳娘秦兰的孩子,奴隶秦安。
是斗奴场的斗奴。
他低垂冷淡的眼眸,一言不发。
裴钰见状更加不悦了,语调也变得尖锐刺耳:
“阿安,我们裴家不欠你分毫,收起你那委屈的小性儿,赶紧随我回府!”
“是,奴才遵命!”
秦安垂下晦暗不明的眼睑,生硬且恭敬的应了声。
“裴安,你够了!”
裴钰的表情并没有多少缓解,反而厌恶地盯着他:“不要让我说第二遍,回府!”
说完,恼怒甩袖,踩着丫鬟提供的软脚凳钻进马车。
秦安低头称喏,跟着裴钰坐上了马车,坐在了作奴的身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