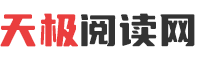话音落,卧房内烛光似晃了晃,隐约不清的身姿仿现出起伏。
“可是看清了?”
依旧是清冷的嗓音,辨不出情绪。
吉祥仔细回忆着,那一幕实在太惊心动魄,实在出不了纰漏。
“是,千真万确。”吉祥想了想,还是将那句二少爷光着身子的话咽了下去。
不能玷污了少爷。
房内缄默片刻,才悠悠传来一句“下去吧”便再无音讯。
吉祥端着烛台,继续守夜。
而屋内,谢景澜倚着榻,半阖眼眸,任由烛光在眼前忽明忽灭。
提着二少爷出去。
他细斟这提着二字,唇边倏溢出冷笑。
今日姜虞月表现如弱柳扶风,夜深倒现出了原形,一介弱女子还能提着一个成年男子出去。
不知明日会上演何等戏码。
他挑灯熄火,卧房陷入一片沉寂。
一夜无梦。
-
天至破晓,谢家府邸前就引起喧嚣闹剧。
早市期间人来人往,皆驻足在谢家门前,八卦打量。
这实乃罕见啊!
光着身子,浑身青紫,还捆绑得别致,像极了那档子不可描述之事。
“你们这群废物,干什么吃的,还不快给本少爷松绑!”
谢进博被下了药,昏迷也被冻醒,一睁眼就对上诸多目光,气得跳脚,奈何被绑得严严实实。
围观群众只敢远观,不敢靠近,各挨着窃窃私语。
“谢家门第清高,怎出的这二公子浪荡性子?”
“这门前挂白幡,大公子头七还未过,真是一言难尽啊!”
“……”
这些话透着风声飘来,谢进博脸色难堪至极。
最终还是谢老夫人拄着拐杖出来,沉着脸命人打发走了看热闹的人群,才算结束。
只是……
谢老夫人看了眼谢进博光着的下半身,沉痛吩咐道:“立刻让张大夫来,切不能让二少爷出事!”
昨日才刚踏出谢家的张大夫,大清早又匆匆赶来。
见此状况,他又抹了把额头的汗,仔细又慎重地查看了几番。
“这,二少爷伤筋动骨,已是无力回天啊……”
“闭嘴!”
谢进博一听,整张脸涨红,恨不得掐死说这话的人。
但他一动,就牵扯到伤势,疼得直抽气打滚。
谢老夫人见状是又气又心疼,“你这浑不吝的,耐不住性子非要跑出去浪,丢尽了谢家颜面,还将自己弄成这副模样!这下谢家绝后了该如何是好!”
一提起绝后这茬,谢进博身体僵住。
憋屈劲儿梗在他心头,嘴唇哆嗦着,却怎么也吐不出个事儿来。
昨夜他根本没去外面,而是去大哥院子里,打算给谢家留个后,却没想到被人揍成了这副尊容。
谢二夫人匆匆赶来,看着自家儿子伤势如此,立刻就掉了泪珠子。
“进博……我可怜的孩儿,究竟是谁将你害成这般模样?!”她凄厉扯着嗓子,“母亲,你一定要替进博做主啊!这府内办丧事,定是让外头知晓了咱谢家只剩进博这一独苗苗,才用此阴损的招儿让谢家绝了后路……”
谢老夫人神色愈加难看,吐出一口浊气,“咱谢家不能绝后,将城里的大夫都请来,不管如何一定治好老二!”
话音落,忽而外面传来动静。
小厮领着二人正欲往府里走,迎面与出门的谢老夫人撞上。
看清来人,谢老夫人面上浮现惊喜之色,“姜夫人,今日可是来探望月儿?”
姜母一身素衣,瞧见谢老夫人露出惊喜,不由几分诧异。
“听闻月儿伤心过度晕厥,我这才想来多看看她。”
谢老夫人连忙喊了他们二人到里边,姜夫人医术高超,当年连难产濒死都将人拉回来,这命根子想必也能治好!
当姜夫人踏入房内,看清发生何事时,神情古怪。
她轻咳一声,视线移向同行的幺子姜桓曦身上,后者即刻意会。
“谢老夫人,不如由我代母亲效劳。”
他上前一步,少年身姿挺拔,颀长的身形已俯在场众人。
谢老夫人这才瞧到这一直跟在姜夫人身后的少年,从前年少还是个豆丁,一不留神就长成俊秀清姿的少年郎。
“好,这位就是桓曦吧?短短不见,竟成如此出色之姿,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!”
姜桓曦轻扯唇角,算是应下。
谢老夫人屏退了其他人,只留他们二人在其中。
姜桓曦冷眼看着又昏死过去的谢进博,伸手戳了一下他下身某处位置。
“啊!”谢进博猛地疼醒。
然翻了个白眼,又晕过去了。
姜桓曦冷不丁笑了下,依这身青紫的方位,笃定了是他姐动的手。
专挑痛处揍。
这第三条腿是定不可能支棱起来了,只不过还得装装样子。
将近半炷香的时间,姜桓曦才缓缓走出来。
谢二夫人立刻迎上去,“我的儿,他……他怎么样了?”
姜桓曦让人拿来纸笔,洋洋洒洒写下一串药方,“伤已至此,只能开些大补的药激一激,事后如何全看造化了。”
听闻有希望,谢二夫人连忙道谢接下,全然没注意到姜桓曦眼底的讥诮。
他开的确是补药,只不过几味药材相冲,这药下去,谢进博定是能立挺些时日。
只不过,是腹泻喷射的那种。
-
北院。
待天全然亮起,姜虞月才悠然转醒。
夜里出了气,当真睡得舒适至极。
听说姜母提前来探望,姜虞月讶异了瞬,便立刻拾掇好,依旧敷粉描虚弱之貌,免得被有心人瞧了去。
姜夫人瞧见姜虞月气色不好,关切问道:“月儿,我观你面色不佳,气血却足,你这心病……”
姜虞月轻笑着摇头,“娘,女儿无事,您不必担忧。”
姜夫人却不似她这般豁达,“月儿,你若是受了委屈尽可与娘说,姜家虽只是富商,但也绝不会任你在这里受欺负。”
一旁的姜桓曦也出声,“那谢进博平日里便色胆包天,现在竟不等出丧就敢出手,废了他真是便宜了他!”
他少年气性,一番话带了极浓的怨气。
“姐,你何时成了这样忍气吞声的性子?之前你还未成婚时,那贼子就屡次在你面前招摇,现在他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,这凭甚不与谢家和离?”
姜虞月听着他替自己打抱不平的话,心里暖了暖。
不过,和离哪是这般轻巧。
姜夫人蹙眉打断他,“胡闹,婚事并非只由一方做主,此话不可再提。”